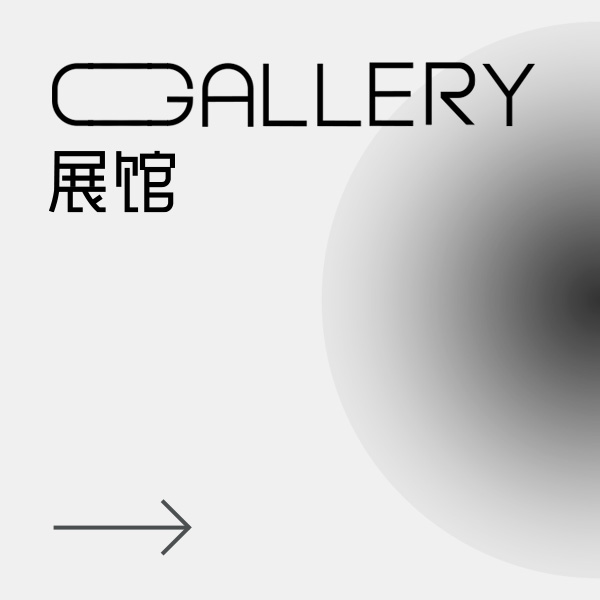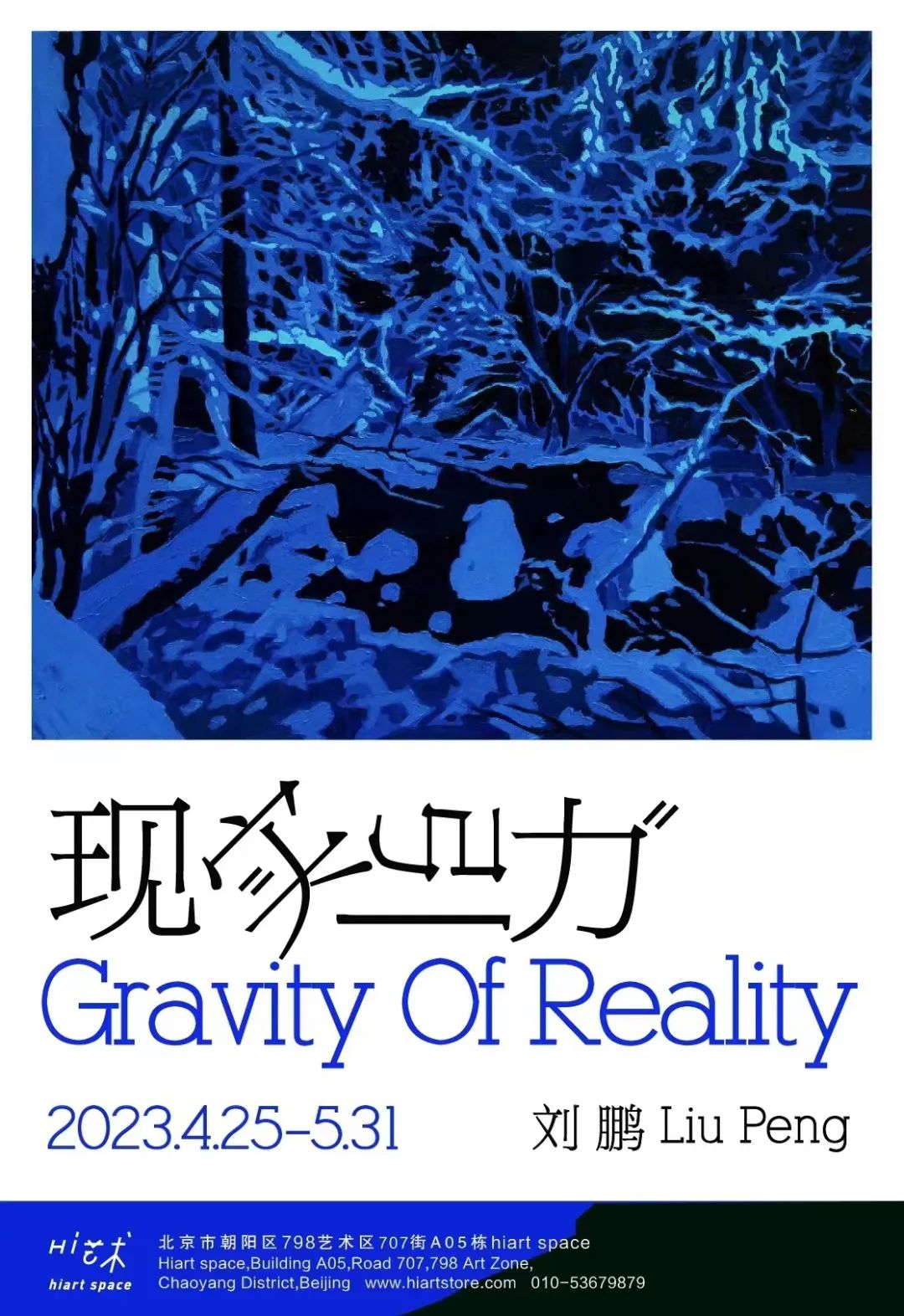作者画廊·北京798
2024.3.15 – 5.2
文/钱文达
距离上一次展览仅仅过去一年,袁佐持续旺盛的创作力,再一次向我们展现出在其绘画谱系中再度生长起的风格推进与言语展现。
袁佐的工作状态,包括这一年多的生活经历,都关涉到艺术实践、生活景观与空间迁移之间的关系。“工作室”成为了无论绘画之内还是绘画之外,这一年多来贯穿袁佐实践经验的关键词和工作线索。当“工作室”被拆解为三个词的时候,字词整体的分离也指涉出一个整体空间的分割层次,即艺术家在面对同一事物(一个工作室在三个空间意义上的错落、转移与变体),但隶属于不同空间的活动轨迹。而这些经验也对应着袁佐面对绘画的一种非比寻常的更新可能与观看方式。
如果说,大部分绘画的终点在于对完成的期待,在于对画面与风格的经营、搭建与收束,那么在袁佐的新作中,我们将被不断进行“破坏”的绘画美学所吸引,这种“破坏”和“消解”成为另外的绘画本能,它重新发掘抽象与具像话语之间的关联,构筑一种本质化的绘画之思。
在这些新作中,我们能看到诸多画面层次之间纷繁复杂的穿插关系。每一笔都是一处空间的自足,激情的起笔,克制的拖曳,颜料开始堆砌、密布,而又不断从中挖空,在几毫米的控制范围内,我们能领略到那多重的起伏差异:笔触节奏的升降、缓急,不同色域的断裂与延续,采用最为熟悉的绘画手段造就为最陌异的微观景域。
《横渡亚得亚里海》就展现出了这样一处复杂的视觉空间。从中间的底层我们看到一个人体的形象,这是袁佐过往积累起的素材(这些素材并无任何叙事符号指涉,它隶属于绘画的单纯),同时,这一形象的完整性并不重要。人体在这里只是一个独立的色块区域,并与上面其他空间层次的笔触和颜色关系进行着绝对的区分。它成为了画幅的基底,成为了初始的画幅元素,画幅层次群落里的第一个层次。这张画从这张人体的色块开始行进,一直走到层次堆叠的尽头。
袁佐在不同空间层次里追求一种空间的极度差异化,每一层次都标志着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觉世界的涌入。笔触的平面化推进与破坏性重构同时存在着,在相对与比对的关系生成中,袁佐发现了永无穷止的实践路径——绘画的趣味不仅在于体会从无到有、从空白到完成的过程,同时,也在于如何尽情地使出浑身解数拉长这一过程,将这过程的空间层次达到极致。
有别于过去注重抽象体验的作品名称,这次部分作品的名字提示出一些非常具体的空间信息,并成为了一个个存在化的景象。当然,艺术家所起的作品名称并不想指出一种绝对的意义关联(甚至叫什么可能对艺术家来说并不重要)。在这幅《烈日才是真正的亚得里亚》中,亚得里亚这一现实经验的提取与其富有重构性的绘画语言形成一种独特的平衡。因此,专注地描绘烈日或者亚得里亚并不是袁佐的首要目的,艺术家所想达成的根本性目标在于画幅本身的结构。当然,这种瞬时记忆般的词汇显现帮助我们了解到关于作品本身之外的额外信息,帮助我们了解到艺术家与作品的另一条支线关联,这种额外信息也恰当地潜藏在绘画本身之中,作为实践缘起的诱因,它让我们确信一副绘画之所以完整诞生的理由根植于一种偶然的遭遇。而这一偶然性恰恰起源于绘画的生命和宗旨。
那些炽热的颜色感受和笔触活力一层层的在画布上进行反复地演示,直到它达成了艺术家所要求的视觉标准(这一严苛的视觉标准又伴随着丰富的灵活机动性)。同时,艺术家在最终确认这一名字的使用中,他会不自觉的从画面中挖掘与之相契合的视觉刺点:温暖弥漫的色调暗示着相应的气候体验;部分理性克制的硬边图形仿佛与一种具体的形象相对应(让我想起优美的海岸风景);既分散又聚合的笔触和线条仿佛在追索不久前的生活记忆。当然,这些信息既重要又不重要,它不以“重要”或者“本质”为自己争得安身立命的话语权,它将在对其有所需要的人们眼里变成作品画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无法被轻易绕过。
与此相类似的提示还有很多,《伊比利亚微风》、《疯狂的龙舌兰让你睡的好》、《按图索骥》……事实上,我们越是从标题回到观看绘画本身,我们越是能够激发、扩大视觉和想象的联结与边界。笔触和颜色在不同画幅空间里的选择与摆置被赋予了永恒的象征性含义,这一含义不断激发着艺术家对绘画语言的试验,对绘画空间层次的探索。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这一年绘画实践所结出的丰沛成果,还有很多在作品与作品之间的联系和空隙中所布局的结构(在绘画活动的静止中,我们也能看到艺术家对绘画的进行)。我不觉得这段时间生活过往的经验是多余的信息和线索,它不意味着我们对于绘画的分心,事实上,有关绘画的操作涵盖于那些隐藏于绘画之外的东西,它作为一种观念的细节反馈到艺术家的无意识行为之中。当绘画的完整生命诞生于艺术家对生活空间一次次的搬离与重新安置时,当生活的意义纠缠于我们对绘画空间的同步理解时,基于外部现实的抽象语言表达将不再是一幅对空的死寂。
就像生活中无形无迹的流动气体被充汇于不同实在的气球之中才可以被看见——根据这些绘画中所凝结的片段与经验,度量世界的边缘和重量由此成为了可能。袁佐的“工作室”成为了一个流动的意象,一个既分离又整合的空间过程,它是标签,是词汇,同时又是在绘画中不断补偿完成的自我意义。绘画与生活成为了互为驱动的生成机制,它们一同自如敞开着,亟待填装视觉的万物。
2024.3.11